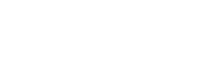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
作为一名曾参与过脱贫攻坚的挂职干部,我看扶贫题材的影视作品是非常容易“上头”的。主旋律影视剧触碰扶贫主题,《山海情》不是第一个。
远一点说,1990年的电影《焦裕禄》可算一例,那是李雪健塑造的经典形象。往近了说,2020年国庆档的《我和我的家乡》,某一些程度上说就是讲了五个脱贫故事,有“社会保障兜底一批”、有“发展教育脱贫一批”、有“发展产业脱贫一批”。不过,《焦裕禄》呈现的是脱贫攻坚的“前史”,虽动人但毕竟距今天有了一段距离;《我和我的家乡》固然在讲好中国故事上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催泪效果极强,但囿于电影的时长,只能在地域上于东西南北中各取一例高度凝练,不及更多展开。
剧情一开始就充满张力,从人尽皆知黄沙漫天的西海固地区涌泉村的“吊庄移民”讲起。“吊庄”是一个形象的说法,类似集装箱起吊一样,把特困区或由于生态原因、工程建设需要而产生的移民,以村庄为单位集体搬迁到有条件安置的地区。这对应的正是后来的生态扶贫、易地扶贫搬迁。从2012年到2020年,中国通过易地扶贫搬迁960多万贫困人口,同步新建约3.5万个类似闽宁镇这样的安置社区。
易地的易,是改变更易,是树挪死、人挪活。看似容易,现实中的阻力很难来想象。与易地搬迁对应的另一种模式是留在当地,那就要进行危房改造、产业扶持、医疗教育帮扶。
要想富,先修路。可是很多贫困县之所以贫困,交通不便都是一块致命的短板。以至于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美景虽好,道阻且长,总是处在可望而不可即的状态。到底是外面的商人进去,还是里面的百姓出来?这又是两个不同的判断。若是前者,修路便是。然而有些深度贫困村,零星的百十户人家在深山老林中组成一个聚落,近乎与世隔绝地过着原始部落一样的生活。究竟是让他们继续隔绝在这里不时受到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威胁,还是请他们搬迁到更适宜人居住的地方?这就是易地扶贫搬迁。
但凡当地的资源禀赋能够承载人口的繁衍生存,自然条件还能适宜人类居住,政府大都不会首选易地搬迁。因为那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自加压力,启动了扶贫的Hard模式,不仅要把人搬出来,还要搬得出、稳得住、有就业、能致富。真正要让搬迁出来的贫困户摆脱贫困,绝不是简单的空间位移所能解决,后续还必须有产业的配套和就业的支撑,还需要基层干部有足够的耐心和高超的工作技巧去做群众的思想疏导工作。
移民只是一个开始,新生的闽宁村遭遇一系列“发展中的问题”。剧情到了这里就由一个微小切口导入到一个宏大问题:东西部扶贫协作。这正是所谓“山海情”的所指。
按照《论十大关系》中的说法,我们的行政结构中不仅有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有地方与地方的关系。这后一种联系看似隐而不彰,却一直是七十余年来维系国家统一和全国经济大局的支柱。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三线”建设、六七十年代的“知青”下乡,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城乡之间的一种特殊互动,同时也留下了东西之间、南北之间、不同地域之间人员、物资、技术流动的历史痕迹。到了1996年5月,中央确定北京、上海、天津、辽宁、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大连、青岛、宁波、深圳等9个东部省市和4个计划单列市与西部10个省区开展扶贫协作,这就是东西部扶贫协作制度的源头。
客观地说,当时所确定的对口关系,有一些是有历史基础的,比如上海与云南之间的帮扶协作,早在五六十年代就开始了。更多的则是类似福建与宁夏这样相距千里且交往不多的地区,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之下,历史性地“拉郎配”到了一起,这就必然有一个相互磨合、逐渐升温直到密不可分的过程。
《山海情》很好地观照到这一背景,塑造了以挂职副县长陈金海和驻村科技帮扶工作队专家凌一农为代表的福建方面的援派干部和专业方面技术人才。他们起初也是壮志满怀,也有政绩冲动,也要面对和处理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循循善诱地引导农民改变思维、走向市场。剧情中这两个人物的人设及其进场和离场的姿态十分妥帖,摆脱了以往同类题材中可以渲染的那种救世主的恩赐心态和施惠者的高大上形象。这恰是东西部扶贫协作的客观过程和效果。扶贫过程不是孤立的、被动的,扶贫者在扶贫中不是被“消耗”,而是发展、成长、壮大了自身,这既体现于个人的思想、觉悟、道德、心灵的升华和澄净,也体现于工作上的能力、经验、方法、作风的提高和历练。
2020年,我曾访谈过一些援鄂医疗队专家,其中一位医生谈到,回来后很怀念在光谷医院那段日子,很纯粹,不用考虑任何KPI指标、利益平衡、部门关系、绩效考核,一门心思就铺在治病救人上,最大限度地从死神手中抢救回一条条生命,那就是唯一的绩效。在某一些程度上,援鄂医护人员的这种体会与扶贫挂职干部是相似的,当每个人的全部精力和才智都在一段时间聚焦在某一个点上,他往往会释放出自己都难以想见的巨大能量。
进而,这部剧的成功之处还在于,塑造了以杨县长、马得福等为代表的一批踏实、担当、有为的基层干部和马得宝、李水花、白麦苗等为代表的一批奋斗进取的青年农民。拔掉穷根,摆脱贫困,最终靠的是内生动力,没有当地人自身的觉醒思变,再多的外部推动也无济于事。
《山海情》的前半段埋下当地劳动力大量输出到福建务工的伏笔——这是短期内快速增收脱贫的捷径,后半段就自然引出留守儿童、“控辍保学”等教育扶贫议题。
留住老师,帮帮孩子,始终是贫穷的地方农村学校面对的最主体问题。所以白校长对厦大过来志愿支教的郭闽航抱怨,希望他能扎下根来,他们一道家访,做辍学适龄儿童的“劝返”工作。白校长甚至误会和怒骂马镇长不该只一味强调劳动力输出的重要性而忽视了教育这个百年大计。这些场景实在是再熟悉不过,那是我在贫困县挂职分管教育期间,每学期开学一段时间的主要“业务”。因为往往就是一个寒暑假,几个外出务工的同龄人的新潮服饰、新款手机的炫耀,就可以勾走一个本身就陷入厌学泥沼的初中生的魂魄,一些班级一开学就会有不少“逃兵”。
教育是斩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途径,也是贫穷的地方最重视的领域。一个类似例子是“海安舅舅”。1988年,一群江苏南通海安人来到云南丽江宁蒗彝族自治县,办一所学校,30余年里先后281名海安“舅舅”接力支教,培养了成千上万当地少数民族儿女。当地领导在全县干部会议上说:“海安教师是我们宁蒗12个民族的亲人,是我们孩子的舅舅,是我们各族人民的舅舅!”在宁蒗家庭,舅舅享有最高的敬畏和尊重,一声“海安舅舅”背后,是宁蒗人民对海安教师的最大肯定。
一般认为云南是上海对口的,而江苏对口的是陕西全省以及青海省的西宁市和海东市。这个案例完全出于偶然,三十年前对方慕名而来找上门,而且当时他们的县委书记是懂教育懂行情懂得到哪里去找人的,说是木材换人材,其实这当然是“不平等交换”,一开始就是帮扶性质,在一个并不在东西部协作体系中具有“法定”对口关系的架构下,不声不响地接力教育扶贫三十多年,让人肃然起敬。
《山海情》是这个年代的一部良心剧,透过那些原生态的土味儿,观众能够感受到剧组对这一主题精雕细琢的求真精神。视频平台上弹幕中的那些90后、00后的“泪目”也表明,自强不息、旧邦新命的脱贫奋斗故事,能够超越时代与世代的间隔,打动每一个人。
写这篇文章时,正好看到朋友圈中一位武汉高校的“挂友”(挂职扶贫干部)发了他的离任感言:“忘不了疫情最严重时,县里向学校无私捐赠的生活物资;忘不了上山下乡步履蹒跚时,走访的农户从柴火堆找出最粗的柴火树枝给我当拐杖;忘不了带着研究生支教团去村级小学开展活动时,孩子们害羞又充满渴望的眼神;忘不了学校捐赠的安全饮水项目完成时,几十年没用过自来水的村民满足又感激的笑容……”
“X年XX行,一生XX情”,这是我们挂职经常听到和说起的句式。“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每当听到当地民歌响起,就如看这部《山海情》片尾曲和字幕时一样,依稀当年,永志难忘。